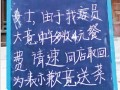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饮食段子,通过考古知识来讽刺人们对古代生活的幻想过于天真浪漫。其大意是说,一个人穿越到战国末年秦国小镇的饭馆,结果啥也没吃成:“牛肉”二字不敢说,私宰耕牛是死罪;铁锅还没发明,小炒无从谈起;想吃主食,面条没有正式诞生,就连蒸白米饭都尚未引入北方,本店只卖小米粥和窝窝头。实际上,很多“汉族传统名菜”的历史并不悠久,比如宫保鸡丁和松仁玉米,两者的原材料都是近几百年才从美洲引进的,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人做梦也想不到能吃上辣椒和玉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餐”比较原始朴素,我们可以从几个汉字的本义略窥一斑。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烹饪”一词,其本义可以说是对“做饭”这一概念最经典的解释:将食物煮熟。“烹”字的本义就是煮,但不一定是用水煮。《汉书》记载:“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其中“镬烹”就是指“下油锅”这种酷刑;如果指明是“汤烹”,则是用开水煮。简言之,“烹”是最古老的食物加工方法之一,它也早早地成为了暴君用来实现恐怖统治的手段,给人们留下了心理阴影,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不再单独使用这个字的原因之一吧。
而“烹饪”中的“饪”,《玉篇》作“大熟”解,表示“食物熟透了”这种状态。可以说,“饪”是“烹”的一种结果,“烹”是“饪”的一种手段。前人选择了具体意指为“水煮油炸使食物熟透”的“烹饪”,来作为“做饭”这一综合概念的代名词,使其本身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当今连生食料理都能被归入“烹饪”的范畴之中了。然而,注重细节的孔夫子是肯定不会允许“饪”这个字被乱用的。《论语·乡党篇》里说“失饪不食”,大概是指君子待人接物要堂堂正正,原则上不吃夹生饭。
难道孔子吃牛扒非要吃十成熟的么?我想他不会这么暴殄天物,适时地“非礼”一下也是可以的。毕竟烤肉在古代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而这种料理方式古人称为“炙”。《诗经·小雅·瓠叶》有言:“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某位贵族的迎宾晚宴上,烤兔头是一道重要的下酒菜,或许也是这户人家的招牌菜。成语“脍炙人口”即是形容优秀的诗文就像美食一样让人忍不住“动口”,它表明“炙”属于当时常识里人人都渴望的美食。
烤肉之“炙”只是“脍炙人口”之美味的一半,资深“吃货”一定不会放过它的另一部分,那就是生肉之“脍”。各种肉类的刺身和抹茶一样,是原本属于华夏民族却又令人费解地被中国主流文化抛弃的饮食门类。毕竟人类文明都是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演进来的,总有人会对生肉料理念念不忘。《诗经·小雅·六月》的记载,周朝军队某场庆功宴上的主菜就包括生鲤鱼片。《礼记》更是系统罗列了食脍的佐料配置——“脍,春用葱,秋用芥”——仿佛中原人吃生肉片的“官方指南”。
所以说,如果穿越回两千多年前的那位仁兄不是进了一家秦国野店,而是被当作贵客请入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这顿饭还是可以吃得很美好的。他可以听着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欣赏着缓缓的歌舞,体验“脍炙人口”的原味。可惜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属于“少数人的历史”,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只能喝野菜羹,啃两口窝窝头,把辛勤劳动的成果奉献给贵族们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