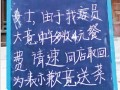旅居异域,何时最思乡?所有人异口同声:用餐即想家。年龄越大,越是怀想母亲的味道。莫斯科友谊饭店,Q君的婚宴,使我在莫斯科偶遇中餐。
亲切、丰富、冗繁,概括了我对中餐的全部感觉。
菠萝古老肉、鱼香肉丝、虾酱豆腐、蘑菇鸡块儿、土豆猪肉炖粉条……久违了的亲昵,让十几位身在异邦的中国晚生,迫不及待地把筷子伸到一盘菜里,把勺儿放进一盆汤里……
土豆、青菜、鱼、肉和鸡蛋,在这顿中餐中,被煎了、炒了、炸了、炖了。五颜六色,鱼香果味地,带着取悦于人的姿色,让我们欢欣不已。已经习惯了西餐的分餐形式,猛然回到这旧有的亲切中,一时间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
中餐最让我感动的是,它让每一位旅俄的中国小朋友,吃在一锅里,用在一盘里,找回了家的感觉,没有了顾忌和界限,每一盘菜都留下十几个人的亲切与口感。可看着剩下的佳肴想打包时,却犹豫了,似乎这时才意识到,亲切过了的美味佳肴,留下十几双筷子的热烈,无法留着下次享用了……
面对满桌杯盘,生出直觉——西餐的简洁明快是我来莫斯科感受最深的。新鲜的土豆、蔬菜,肉蛋,不论怎样的加工,鱼香肉香,都各成系统。即便是烧烤出来的猪排、牛排,也只是在这种肉类固有的质地中,加放了新鲜的洋葱、番茄、胡椒与盐,没有强行的人为味觉,一块牛排,两根香肠,一盘沙拉,再加少许面包和汤。恪守各自的品质,入腹后少有发酵过程。餐饮时,刀、叉、勺各得其所,将需要的饭菜,用特定的刀叉小心地拨到自己的盘中,小口吞咽。没有人会把从口里拿出来的餐具复放进共享的饭菜里。剩余的饭菜始终都保持清洁,下顿食用自成习惯。从这点看,中餐的两根竹筷子简单地替代了刀、叉、勺的各种功能,一筷在手,堪称万能,伸到不同的盘中,直接取食,快捷食用。亲切了,却又……
另从进食而言,西餐以刀叉切割食物,小口吞咽,寂静无声,以吃出声为尴尬,为教养不良。中餐则将附加的味觉,通过烹饪渗透到鱼和肉的每一个毛孔,文化渗入,使食用者,品咂之声,不绝于耳,视之为快。
我还发现,西餐吃后,打嗝情况很少,中餐却很多。不知跟大口吞咽与多种食物搅拌、发酵的作用是否有关?
总之,不同感觉,文明呈现现大异。上述种种,恐有崇洋媚外之嫌,出来几日,就中餐长西餐短的,妄加评断。其实,我也只是把感觉记下,关起门来说话,没有对错。就想着:喜欢西餐,以后多吃点,喜欢中餐,以后多做点。况中国开放后,正在加快与世界相融的时间和速度。能够在生活习惯上取长补短,也不啻为一种大国的谦虚和包容,因为,文明的程度,不在于你的腰包里装了多少硬通货,更多地还在于生活细节中透露的——一个民族骨子眼里的素质与素养。